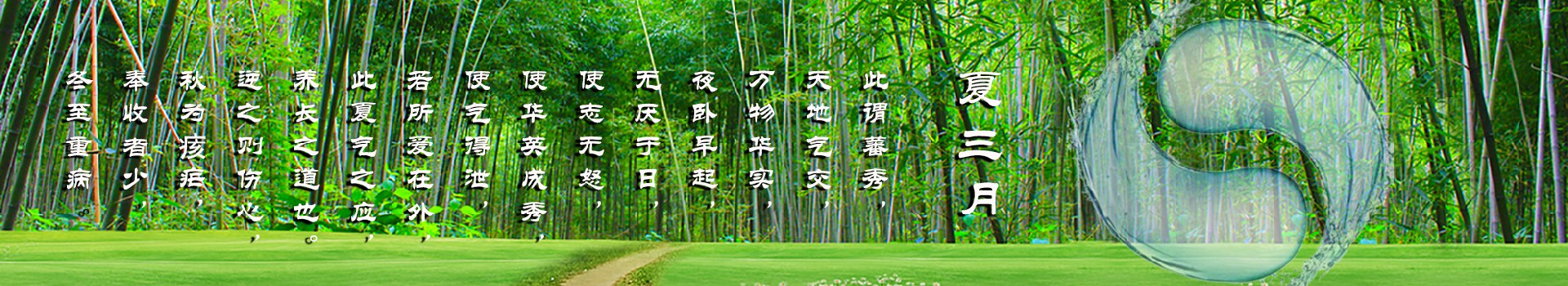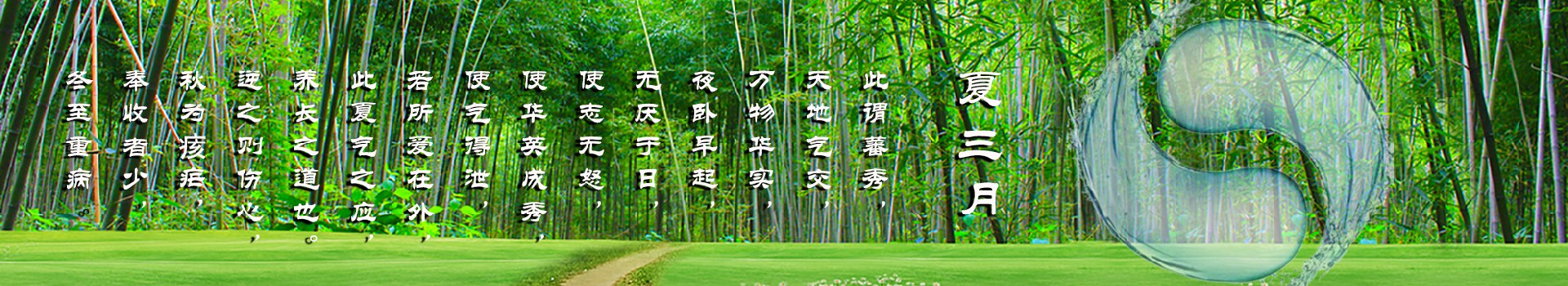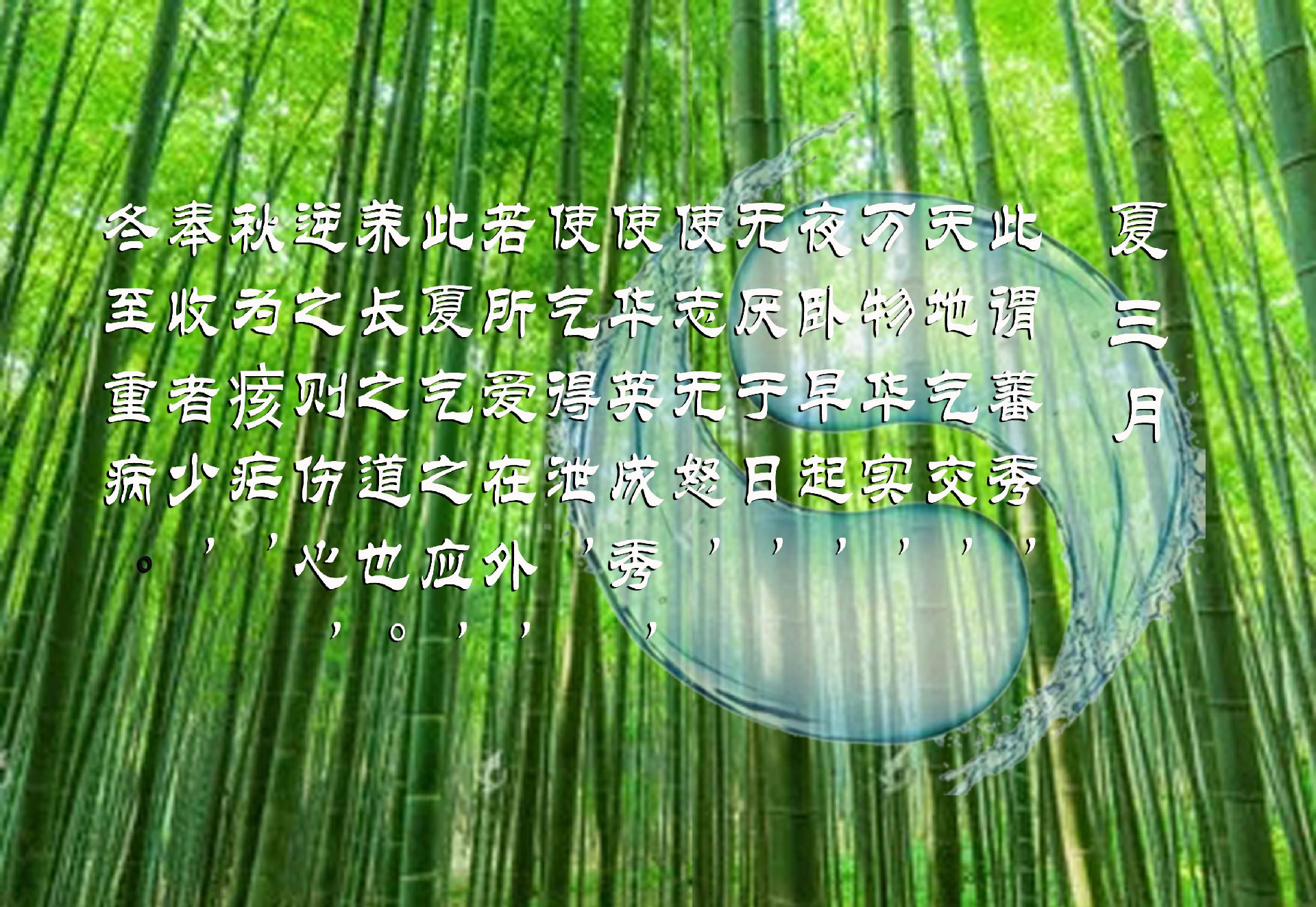物理學之道與“中醫(yī)現代化”(中國中醫(yī)研究院,傅景華)
類別:最新動態(tài)
更新時間:2013-05-04
瀏覽次數:3331
中醫(yī)太極網
1、二十一世紀風暴
1900年��,在那西方科學界充滿自信和驕傲的歲月里�����,經典物理學晴朗的天空中出現了“兩朵烏云”����。誰都不曾料到��,在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和黑體輻射的陰影下�����,竟然突發(fā)了一場亙古以來最為強大的“二十世紀風暴”����。1905年以后,相對論和量子論在令人眩目的震撼中相繼誕生����。牛頓的機械力學體系,連同那絕對時空的觀念和拉普拉斯的因果決定論��,由之而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zhàn)�����。
與此同時,以嚴密性和無矛盾性著稱的數學��,因德國數學家康托爾創(chuàng)立的集論而引發(fā)了第三次危機�,并直接危及到整個數學大廈的安全。(在此之前��,數學大家庭曾度過了畢達哥拉斯學派信條的否定而出現的第一次危機和牛頓���、萊布尼茲所創(chuàng)微積分中無窮小量的爭論而形成的第二次危機)1902年��,著名的羅素學論又以其簡捷明確的描述而震動了整個數學界��。
1926年���,薛定諤發(fā)現了激動人心的波動方程。海森伯(Werner Heseaberg)等創(chuàng)立了矩陣力學的數學形式體系�,并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不確定性原理。從而導致了震驚世界的“EPR”佯謬�����,以及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與玻爾(Niels Bohr)之間空前規(guī)模的論戰(zhàn)��。
愛因斯坦認為量子力學沒有確定的基本原理���。玻爾學派認為量子力學的經驗性不是理論的缺陷�����,而是理論的優(yōu)點�。測不準原理�、可觀察性原理、互補性觀念����、幾率性概念等展開了對完備性、明確性���、清晰性��、精確性的挑戰(zhàn)����。這場巨人的爭論吹響了新的科學革命的號角�����。
2、第三次革命
本世紀中葉以來�����,現代自然科學之母一一數學和物理學又掀起了驚天動地的變革�����。迫使整整一代智慧的心靈必須再一次接受那描述大自然的新觀點�����,科學家們的世界觀從此將發(fā)生劃時代的轉變����。包括一般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以及自組織理論����、等級層次理論等嶄新的系統(tǒng)科學思想,組成了群星璀璨的世界�。
從簡單到復雜,從局部到整體����,從結構到狀態(tài),從無序到有序�����,從沖突到協同����,從分析到綜合,從平衡態(tài)到非平衡態(tài)�,從線性區(qū)到非線性區(qū),這些最富有革命性的理論揭示了一系列絕異于西方傳統(tǒng)觀念的新的本體性原理和范疇�。
深入展現生命世界的復雜性,是系統(tǒng)科學的重大成就��,同時也把生命目的性的探索推進到一個新的深度和廣度�����。整體不再被分成部分��,系統(tǒng)不再被分成要素,結構的分析轉換為狀態(tài)的綜合�,真理的確定轉換為似真的描述,經驗事實的實驗證實已不再是科學研究不變的信條���,實驗室的生化指標已不再是科學研究所追求的目標�,定量化的標準已不再是科學研究的唯一標準�,客觀化的規(guī)范已不再是科學研究的唯一規(guī)范。
以埃利雅·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為代表的布魯塞爾學派用遠離平衡態(tài)的非線性區(qū)的“耗散結構”揭示了開放系統(tǒng)與環(huán)境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并引進負熵而實現自身的有序過程����。德國教授哈肯的協同學則揭示了系統(tǒng)內部各要素如何實行協同與合作�。1971年艾根創(chuàng)立的超循環(huán)理論認為生物的生存與發(fā)展基于物質、能量���、信息循環(huán)中實現的自組織過程�。法國數學家勒內-托姆的突變論則為描述大量不連續(xù)現象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于是一個開放�、協同、有序�、循環(huán)發(fā)展的新世界圖景便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既然如此��,科學知識已不再是基本定律��、基本原理�����、基本概念為基礎組成的��,建筑在粒子物理學家丘(Geffrey.Chen)所創(chuàng)立的“靴帶”理論則完全同基礎科學的西方方法決裂�。該理論不承認物質的基本組成要素�����,徹底放棄了基本建筑塊的思想����,而且也不承認任何基本的常數�����、定律和方程���,把宇宙及生命看作相關事件的動力學網絡。從而被譽為現代自然科學的“第三次革命”(也有的科學家稱近年來興起的混沌論是現代自然科學的“第三次革命”)�。
3、神往東方之道
現代物理學的世界觀轉向竟如此迅猛�����,如此劇烈�,使整個科學界為之震驚。1959年海森伯發(fā)表了《物理學和哲學一一現代科學中的革命》�,把這場偉大的科學革命引入哲學和思想文化領域。1962年��,庫恩(Thomas kuhu)發(fā)表了《科學革命的結構》�����,以全新的科學史觀點揭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二十世紀不斷掀起的物理學風暴已席卷全球�����,并日益深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角落�,世界處在深刻而又廣泛的危機與變革之中。
然而�����,一個令人振奮的歷史性發(fā)現引起了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們的濃厚興趣����。正在以磅礴的氣勢驟然興起的新科學觀與中國古代的科學哲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有的科學家甚至認為目前發(fā)生的這一變革是向道家思想的歸復���。海森伯承認東方古代思想和現代量子論的哲學結論之間的關系一直對他有極大的魔力。物理學家惠勒(John wheeler)認為:人們已感覺到東方思想家所認識到的一切�����,并且如果我們能夠把他們的答案翻譯成我們的語言��,我們將得出我們所有問題的答案���。
美國粒子物理學家弗里喬夫·卡普拉(Fritjot Capra)于1974年發(fā)表了《靴帶和佛教》��,于1975年又出版了《物理學之道》���。他認為:基礎主義者和靴帶論者之間的矛盾反映著西方和東方兩大主流思想之間的矛盾��。道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永恒運動的循環(huán)性���,道的一切顯示都產生自陰陽兩極的相互作用,道作為基本的實在是一個連續(xù)的流動和變化的過程?,F代系統(tǒng)論的觀點顯示著向中國古代思想歸復的特征,體現著老子的偉大的生態(tài)智慧�����。I
1972年��,巴特生(Gregry Bateson)出版了《走向精神生態(tài)學》����,把精神定義為“生命事物”的系統(tǒng)現象特征。用系統(tǒng)觀�、生態(tài)觀取代笛卡爾一牛頓的機械觀來認識生命活動,是本世紀生命科學的重大轉移�����。普里高津以自組織系統(tǒng)理論來看待生命現象,并把對結構的研究轉向變化過程��,于1980年發(fā)表了從《從存在到變異》�����,廣泛吸收了《易經》和道家著作中的思想�����??ㄆ绽谖髅深D(Garl Simonton)和洛科(Margaret Lock)的影響下����,研究了中醫(yī)學中“氣”的概念,確立了整體論的健康觀�����,于1981年出版了他的《轉折點》���。書中批判了生命的機械觀和生物醫(yī)學模型��,揭示了生命的系統(tǒng)觀���。醫(yī)學領域的思想革命�����、范式轉移���,以及其向中醫(yī)理論的逼近,已成“橫弩”之勢.�。
4、科學史上的奇跡
人類認識突飛猛進的發(fā)展�,以其洶涌澎湃的浪潮沖決了“無可奈何”的機械世界的堤壩,卻越過了一個“似曾相識”的新世界的門坎���。人們早已習慣了第一世界那平坦的空間��、均勻時間�����、不變的質量�、單純的能量、低速的運動�����、可見的軌道���、有形的實物�、固定的結構����、定量的指標、漸進的發(fā)展��、平衡的關系�、線性的知識。而現在又不得不面對無數令人眼花繚亂的“反?��!钡男率澜鐖D景,難怪有人目瞪口呆�,無所適從。
空間是彎曲的����,時間是不均勻的,小而可變的質量,大而相干的能量����,超高速的運動,不可見的軌道��,無形的變化���,沒有固定的結構�,更難找到精確的“客觀指標”��,宇宙和生命是突變中的非平衡態(tài)����,是非線性的自組織的有序系統(tǒng),還有那場���、信息���、狀態(tài)、熵�、網絡、集合�、概率等……���,一大群新思想、新概念象潮水一樣劈頭蓋腦地向我們撲來�����。然而�����,第二世界宏微觀領域的大門似乎才剛剛打開��。哲學家波普爾“三個世界”的理論在科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把研究對象稱為第一世界,把實踐主體稱為第二世界�����,把精神產品稱為第三世界����,這只是科學研究中的分界��。那么千變萬化的自然界是否也有一個“第三世界'?在東方中國那遙遠的時代���,先哲們仰觀天象����,俯察地理����,中及人事,專注偉大的生命意識����,洞悉那錯綜復雜的宇宙人生。從而發(fā)現了在形氣陰陽兩個世界之外�,還有那“陰陽不測謂之神”的奇妙的境界。在這里��,“質量”接近無限小����,“速度”接近無限大,”形態(tài)“接近于無�,“能量”達到超能,包括時空在內的許多基本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概念都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而生命、意識��、精神����、情感、“特異功能”等���,以及那無數不解的宇宙之謎�����,卻有可能在這里找到它們最終的歸宿����。
大至天體的追尋�����,小至夸克的求索��,人類對生存外環(huán)境的了解日新月異���,但卻往往在改造自然的勃勃雄心中迷失了自己����。然而����,中國古代那氣勢恢宏的道家思想、博大精深的中醫(yī)理論��、神奇莫測的氣功導引����、無以倫比的內家武術,卻對生命自在的研究獨樹一幟���,創(chuàng)造了人類科學史上的奇跡�。遺憾的是�����,中國人專心致志地潛心進行生命的開發(fā)達五千年之久��,卻難以走出近代百年的塵封而重放異彩�。(人類對自然的認識無疑是“兩條腿走路”的)
科學的描述可分為結構的描述�、狀態(tài)的描述和過程的描述?��,F代自然科學由結構向狀態(tài)的轉移�,進入了系統(tǒng)科學和生態(tài)科學的新時代�。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和超循環(huán)理論就注重研究自組織與系統(tǒng)運動狀態(tài)及相空間(狀態(tài)空間)�����。狀態(tài)函數的概念和狀態(tài)空間分析方法迅速向所有的學科滲透�����,最富普遍意義的“信息”就是狀態(tài)學的概念�����。維納斷言:信息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
中醫(yī)學研究人的生命過程及其各種運動方式的相互作用,把生命的自我實現、自我發(fā)展及發(fā)展的和諧作為醫(yī)學的根本目的�����。中醫(yī)學的概念是過程的概念�,中醫(yī)理論的描述是過程的描述���。如廣義的氣可代表無限的運動方式�,狹義的氣可代表各類不同的生命運動方式�����,陰陽則代表兩類相反相與的運動方式�����。五藏理論反映五類生命運動方式的相互作用�,遵循生克制化的五行序列規(guī)律,腎心肺肝脾可代表生命活動的發(fā)生����、動力、轉換�、協調、演化過程�����,而絕不是僅指組織器官…。
中醫(yī)學中也不乏狀態(tài)的描述及結構的描述��,中醫(yī)病機學關于虛實�、寒熱、燥濕態(tài)勢和表里出入�����、上下升降�、開合聚散趨勢的理論就是狀態(tài)的描述。而關于三陰三陽六病分類及衛(wèi)氣營血��、三焦的辨證理論����,則是時態(tài)的描述。中醫(yī)學重道輕器����,重氣輕形,對結構的描述最為輕視���,而以過程的描述為主導�����,這正是未來科學發(fā)展的方向�����。
5�����、走向西方之路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可通約性原理:似乎同樣的術語在不同的范式里沒有同樣的指稱��,屬于不同范式或產生不同范式的理論對應著不同的世界��。費耶阿本德也有類似的看法:一個術語在不同的理論中既沒有共同的指稱�����,也沒有共同的意義�。中醫(yī)學與西醫(yī)學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疇屬于不同的范式�,對應著不同的世界。同樣的醫(yī)學術語在不同的醫(yī)學理論中具有不同的指稱和不同的意義����。更何況是中國的西醫(yī)學者在翻譯西醫(yī)學時借用了大量與之不相容的中醫(yī)學術語�����,而反過來又用這些完全改變了內涵的西醫(yī)學概念來解釋�����、驗證����、衡量和鑒定中醫(yī)學�����,從而引起了一場令中西醫(yī)工作者和所有觸及醫(yī)學的人們都感到十分困苦的歷史性誤會���。然而����,中醫(yī)學的現代研究卻認為:氣���、陰陽����、臟腑、經絡�、證等抽象名詞概念,只有以實證分析法研究其細微存在形式與具體變化�����,才能給人以形象的理解��。中醫(yī)氣����、陰陽、臟腑��、經絡�、?quot;實質“的研究及”物質基礎”的研究因之而全面鋪開��。補短論者認為:中醫(yī)學必須開展人體結構和功能的研究��,以彌補自己的不足�,在器官、組織�、細胞水平進行多指標��、多途徑的研究����,將為中醫(yī)理論最終與“現代科學”及“現代醫(yī)學”語言的同化奠定基礎�����。長于過程研究的中醫(yī)學不得不重新走向400年前由伽利略�����、培根等西方科學家開辟的以還原分析法研究實體結構的道路�����,并不畏千辛萬苦地在實驗室中摸索前進����。
量子論為當代科學帶來的最大變革,在于發(fā)現物理量具有本質上的不確定性���,從而導出了著名的測不準原理�,要想精確測定粒子的位置��,就不能測定其動量;要想精確測定粒子的能量����,就會失去時間的精度。要使一方“精確”�,就得“犧牲”另一方。于是在愛因斯坦與玻爾的論爭中發(fā)現了意義深遠的互補性原理�����。(盡管這一原理早已成為中國古代科學家們的常識)顯而易見�,中西醫(yī)學卓然自立,在實踐應用中相反互補地結合��,理應成為醫(yī)學工作者的常識���。精確性與清晰性的要求導源于笛卡爾的傳統(tǒng)���。為了達到這一要求�,人們認為中醫(yī)學必須具備以物質性質為具體標準的實驗客觀指標和精確數據,才能說明中醫(yī)理論的“嚴密性”和 “科學性”�����。于是,西醫(yī)學的客觀化���、規(guī)范化����、標準化���、定量化便成為對中醫(yī)理論的基本要求�?���!安幌到y(tǒng)”、“欠精確”����、“經驗型”向定量化、客觀化的轉移被認為是中醫(yī)研究方法的質的突破�����。通過實驗證實����,用“現代醫(yī)學”和“現代科學”語言闡明中醫(yī)“實質”����,已成為現代中醫(yī)研究的主要內容��,亦即是“中醫(yī)現代化”的標志��。
中醫(yī)學的概念被認為沒有結構依據�,由于中醫(yī)未能深入細胞、分子水平��,所以有人認為必須從微觀入手�����,打開“黑箱”���。為使人們都能理解和接受中醫(yī)理論�����,被解釋成“自發(fā)”�、“樸素”�、“原始”水平的中醫(yī)學便需要拋棄���。既然時代和文化背景已發(fā)生改變�����,人們又要求中醫(yī)學從根本上即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科研方法上達到與新文化背景的統(tǒng)一����。鑒于以上論點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普遍性�����,因而使中醫(yī)學在重復西方之路的艱難跋涉中一再路入“普洛克魯斯特床”的重重危機���。
6��、尋找另一半
在那古希臘迷人的寓言王國粒�,由大哲學家柏拉圖召開的《酒談會》(Symposium)上,亞里斯多芬尼斯講述了流傳千古的人類愛情原動力的童話�����,自從宙斯把圓柱人中分為二以后����,那保留著原始記憶的人們,便無休止地渴望與本身的另一半會合��,并強烈地希冀與之融為一體��。
現代物理學最先從傳統(tǒng)的結構與功能的研究基地分離���,進入了系統(tǒng)與要素��、狀態(tài)與信息研究的嶄新領域�����,并盡力向古代東方的思維方式和中醫(yī)學的科學思想靠近��。而現代中醫(yī)學則幾乎遺棄了自己關于過程與方式的生命研究范疇���,力圖深入西醫(yī)學研究對象的人體結構與功能的內部世界�,以期實現那忘我的結合���,這一奇特的景象仿佛是人類本體性的結合意識在神圣的科學史上的重現。
然而�,前者猶如一個主體性的開放系統(tǒng),欲結合對方��,為我所用�����,以實現自身向更高層次的發(fā)展�����,而后者則欲消融自己�����,以求化而為一����。那“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追尋感人至深,但卻總是難以排除那“剪不斷����,理還亂”的彷徨與困惑���。
東西方文化的長期隔絕,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不斷分離����,理論的不可通約性,自然本質的不確定性����,特別是語言的障礙,使東西方都企盼的文化交匯任重而道遠�����。正如惠勒所感覺到的翻譯困難和遺憾一樣�����,著名科學史家柯瓦雷在“科學思想史研究方向與規(guī)劃”一文中告誡人們:必須抵御這種誘惑一一已經有太多的科學史家陷于這種誘惑之中一一即為了使古人的思想更易理解而將其譯成現代語言�����,盡管“澄清”了它�,卻也同時歪曲了它��。
當代人類知識的大廈在科學支柱的不可扼止的膨脹中急劇傾斜�����,為了追求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融合��、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匯,科學人文主義悄然興起�����?���;谶@同一傾向的中西醫(yī)結合與“中醫(yī)現代化”,就象當代最新科學理論對古代道家和中醫(yī)學思想的追求一樣�,乃是人類對于統(tǒng)一與有序,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的共同向往����,因此問題根本不在于要不要中醫(yī)現代化,要不要中西醫(yī)結合�����。而在于怎樣現代化,怎樣結合�,在什么樣的思想指導下,以什么方式結合��。宇宙和生命的內在統(tǒng)一性���,決定了自然科學的革命實際上就是生命科學的革命實際上就是生命科學的革命���。隨著最新科學理論向系統(tǒng)科學和生態(tài)科學的進軍,未來科學的目標已指向東方文化與中醫(yī)理論及其哲學思想����。如果以生態(tài)學和過程論的觀點理解和發(fā)展中醫(yī)學,在生命研究的領域內��,則可完全打開再未來科學的層次上實現東西方文化交匯和中西醫(yī)結合的通道�。
物理學家狄拉克倡導的“創(chuàng)造美的理論是最重要的”。自然的深處有著美的簡捷的法則�����,有美與和諧���。追求這一自然的真諦是科學的本質��?�!岸兰o暴風雨”喚起了科學天空瑰麗的彩虹����。密爾頓和鮑波那充滿激情的詩篇贊美了科學的統(tǒng)一與和諧,“靠人的智慧解開宇宙與生命之迷的時代已經到來”��。